文/科工力量 李沛
浦东金桥,华为上海研究所。
华为智能汽车业务部2000多名工程师,已经在这里默默无闻耕耘了7年时间,这是一支国内,乃至全球规模最大的自动驾驶汽车工程研发团队。
他们的工作成果,即将惊艳世界。
4月15日,华为自动驾驶解决方案(ADS)首款量产载车,邀请媒体进行了试乘体验。
无保护左转、窄路会车、规避行人和外卖小哥...在路况复杂多变的市区,开启ADS系统的载车全程无需人工介入,流畅妥当地完成了一系列处置。

(在“占领用户心智“上独步天下的特斯拉,在自动驾驶的真实能力积累上还”任重道远“)
2016年,福特和百度曾共同向硅谷激光雷达头部企业Velodyne注资1.5亿美元,用于帮助后者加速下一代激光雷达的开发和制造。
不过让人感慨的是,华为却后来者居上,率先实现了激光雷达“白菜化”的目标。
搭载于量产载车的华为96线车规级的激光雷达产品,一套仅需200美元,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价格,较之现有类似性能车规产品便宜了一到两个数量级,华为方面还表示,计划在两年内把价格进一步做到100美元以下。
对于自动驾驶“感知”环节技术路线的特立独行,特斯拉方面的解释却相当“文艺”,李飞飞弟子,特斯拉自动驾驶算法总监卡帕蒂(Andrej Karparthy)直接将之升华到了世界观层面,Karparthy认为,既然人可以靠眼睛来开车,机器也没有理由做不到,甚至没有理由不这样做,激光雷达尽管“确实是(自动驾驶)捷径”,但特斯拉就像最优秀的做题家,只愿意解答计算机视觉这道“终极问题”。
如果是作为象牙塔里学者来说这样的话,Karparthy尽管有走火入魔之嫌,不过寻找神经网络算法 “圣杯”的心情情有可原。
但特斯拉作为一个向顾客交付高速交通工具的企业,用这样的言辞管理公共关系,只能说是对同行,对客户的智力太过于缺乏尊重。
在4月15日的媒体活动中,针对感知层的技术路线之争,华为自动驾驶研发团队负责人苏箐,也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这位在华为工作了二十多年,于麒麟、昇腾芯片项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技术精英,回答这个问题显得颇有“直男”思维:
“大数据的重点不是‘大’字,是数据质量和全,这个是大数据的本质,自动驾驶其实很像。数据里面两个问题很关键。第一,数据本身的质量。第二,数据的维度。在这两个问题上,我觉得特斯拉的数据有大问题。什么叫维度?仅仅靠简单的几个视觉搜集的数据,这个数据高精定位什么都没有的时候,维度是非常低的。明显看到 ADS 的车数据维度比它高好几个数量级...你低阶系统本身复杂度导致数据本身质量比较低,特斯拉目前是在这个状态,要我猜,特斯拉的数据早就饱和了,对系统能力没有提升。”
从科工力量对业内专家的访谈,以及我们自身实际搭建过神经网络项目的切身体会,苏箐的回答可以说点出了自动驾驶感知问题的关键。

(苏箐这样解释华为MDC的产品思维:“传统的车厂他的看法首先我的基座是车,现在有些计算机的单点,那么我是把车作为一个基础,然后我试图把计算机嵌进去,这是传统车厂的看法。我们的看法不一样,我们的看法基础是计算机,车是计算机控制的外设,这是本质看法不一样,会导致所有事情看法都不一样。”)
华为智能汽车电子产品(Huawei Inside)更重要的意义,在于通过自动驾驶功能的牵引,实现了整个汽车电子系统架构的重塑。
试驾量产车上搭载的华为智能驾驶计算平台MDC,从形状上看就像一个普通的小型台式机机箱,集成了运算、控制、存储、通信等芯片,并且具备车规级的品质和功耗控制。
在功能上,MDC也可以理解为一个“电脑主机“,从接收探头、雷达、通信等硬件数据,到运行自动驾驶的三大功能模块,感知、预测、PNC,再到策略形成后向转向、驱动,制动等行车硬件的输出。
这样的系统架构,在消费电子产品上看起来稀松平常,但在汽车电子领域,却是一场巨大而深刻的变革。
“特斯拉终于遇到一个技术实力和忽悠能力旗鼓相当的对手了”
华为自动驾驶解决方案正式登场,以战略洞察力著称的美团创始人王兴,随即在社交平台饭否发表评论,“特斯拉终于遇到一个技术实力和忽悠能力旗鼓相当的对手了”。
华为为什么要做自动驾驶?
与外界普遍的解读,即应对外部制裁的被动“战略大转移”不同,华为早在2014年,就在内部预研部门“2012实验室”组建了车联网团队,实质展开了车联网、智能汽车技术研发,苏箐领导的自动驾驶ADS团队也开始起步。
而在这一年,特斯拉的所谓“自动驾驶”硬件:12个超声波传感器、一个毫米波雷达、一个前置摄像头,才刚刚开始装车,著名的7.0版本固件升级还要等到2015年年末。
华为的“先知先觉”,并不只是巨型科技企业在新技术方向上“下闲棋,布冷子”的常规做法,而是有着为公司未来主要业务探路的明确诉求。
当时的华为,仍然是一家典型的通信设备企业,运营商业务占据其营收的三分之二份额,面对运营商4G网络投资进入后半程,5G网络还有相当不确定性的战略环境,华为迫切需要寻找未来能挑起大梁的新主营业务。
尽管智能手机为核心的消费者业务势头喜人,但体量上还并没有建立起对其他业务方向的绝对优势,汽车电子,是华为企业业务一个有吸引力的开拓方向,直白的说,华为需要转型,汽车电子也是一个适合切入的新市场。
全球汽车电子市场,尽管不及消费电子市场,但仍然是一个体量2000亿美元以上的巨大蛋糕,其中的佼佼者如博世,年营收也可以达到700亿美元以上的惊人水平,随着新能源汽车,特别是纯电动汽车的兴起,汽车电子市场原有的竞争壁垒出现了明显松动,内燃机时代电喷、EPS等动力控制、底盘控制、车身电子等一级供应商和整机厂的密切关系开始解耦,为新竞争者进入提供了可能。而驾驶辅助、车上娱乐等需求带来的车载电子这一增量细分领域,消费电子厂商较传统汽车电子供应商反而具备更强的竞争力。
从商业实践上看,消费电子企业向汽车电子的转型也并不罕见,曾经的北美智能手机产业霸主黑莓(Blackberry),在后塞班时代的市场混战失败后,由2013年上任的华裔CEO程守宗(John Chen)主导,开始果断剥离智能手机硬件业务,向企业软件和汽车电子市场转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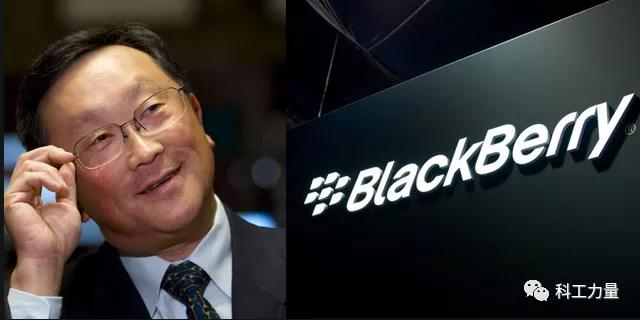
(加特纳炒作周期,人性、商业与技术的潮起潮落)
按照加特纳曲线的轨迹,行业“虚火”退潮的冰河期里,技术要素渐趋成熟,市场要素渐趋优化,最终将带来行业发展的“第二波”爆发,出现真正可行的商业模式及领军企业。
从技术史和商业史上看,加特纳曲线的前半段几乎是一种有关人类社会群体运动的真理规律,而加特纳曲线的“第二波”,则并非必然会发生,产业拐点,或者说正式起飞(lift off)的“第二波”,依赖于三个必要前提:
1,有领导力的企业
2,关键技术成熟
3,出现“杀手应用”场景
除了特斯拉这个市场公关和技术路线的双料“奇葩”,自动驾驶产业毫无疑问遵循着加特纳炒作周期的轨迹,2020年,这一新兴产业的“紧日子”俨然已经达到最低谷,优步公司低价割肉,拆分了其自动驾驶业务,谷歌Waymo也一度盛传将被抛售,高度可疑的Robotaxi,即给定区域无人出租,似乎是唯一一个可能承接行业落地的小“池塘”。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华为ADS量产车的登场,改写了行业图景。
对照新兴技术“起飞”的三大要件,华为的横空出世,证明了:
1,这家巨头明确的入场意愿和激进规划
2,激光雷达、车上算力等成本、功率“关键难点“的突破
3,城市道路无人驾驶这一“杀手级应用“
更重要的是,汽车电子的未来想象空间,不止在车,还在路。
依托车联网基础设施的车路协同,是华为,乃至整个中国智能汽车产业界,有志一同的战略发展方向。
从工程角度看,单车自动驾驶的功能实现,固然可以在完善的传感器和车载算力支持下达到相当水准,但是“超视距“,也就是超过视觉范围的路况感知,比如前方车辆挡住的外卖小哥,或者前车前方的突发事故,对单车而言,仍然是不可能的任务。
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个极度简化的场景,假如有一个路边高架摄像头,可以识别半径100米内人员车辆所有活动轨迹,并将相关信息通过5G网络传输给途经车辆,这样,汽车无需搭载完善复杂的传感器套装,就可以实现对周围环境更完善的感知和决策规划,更进一步的,再能够车辆之间或车路之间通信的情况下,车辆的驾驶意图可以相互传输,从而极大减少预测规划的算力负担。
显而易见,将车辆联网,车路联网,是自动驾驶真正普及的必由之路。

(已经形成了中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创新联盟、中国汽车工程学会、中国移动、华为、百度等组成的产学共同体)
车路协同的前景虽好,真正将之实现却远远超出了一个企业的能力,它考验的,是一个国家的战略意志。
美国在城市开放道路车路协同演示和车联网通讯标准制定上,几乎都是最早的先驱者,然而在今天,推动车路协同最大最持久的力量,却来自中国。
华为ADS载车惊艳表现的背后,是上海在智能汽车产业化上的巨大扶持力度,去年7月,浦东金桥开发区划出了上海市首个中心城区自动驾驶开放测试区,这也是国内超大城市中心城区率先开放的智能汽车开放道路测试场景。
在金桥申江路、东靖路等十多条规划道路上,不仅是华为ADS,其他国内整车厂和方案商的测试车,同样已经频繁可见,这里,已经成为中国智能汽车产业的一片热土。
车路协同驱动的道路智能化改造,同样将为华为提供巨大的转型机会。
根据保守估计,每公里100万元的道路智能化改造成本,中国公路网的智能化改造,就将创造一个新的千亿级增量市场。
华为,乃至中国智能汽车产业,在4月的“初试锋芒”后,还有一个又一个震撼人心的技术成果将呈现在世人面前。
我们拭目以待。
《科工力量》的付费专栏,最近上线了,我们将用23讲的内容,基于中国视野,全面解析全球供应链变换之路。从中国工程机械产业逆袭、到高铁大飞机的落地、再到芯片行业的血雨腥风,一个个精彩甚至离奇的故事,见证中国制造业的崛起。

花粉社群VIP加油站
猜你喜欢